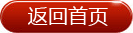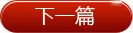還是上小學的時候,對天柱山這個字眼就有所特別的記憶與理解,記得最初好像是作為一家地方報紙文學副刊的欄目名稱。其實那時識字還不多,好在這三個字都很容易認得,望文生義吧,在心中想當然地就給這座山定義著一份神秘,一座比之天高的山。
歲月流連,一直想去見識見識這座神奇的山,可終沒能如愿,兒時的夢想一擱就是二十多年,恍惚中那高聳入云的天柱總是浮現在眼前。
去年深秋的日子,我背負清晨的陽光,也背離浮華喧囂的城市,秉著心中的依戀,輕輕地踏上了大別山的南麓,和皖水迂繞的大山有了一個照會。
沿著石級古道,踩著秋日的露水,山上的空氣里有一股甜絲絲的味道,行進中給人一片清新。路上游人不多,顯得格外清靜,只有林間飛鳥在雀躍,撲通通聲里也正是在舒展著人的心情。這個季節早晨似乎顯得有些涼意,前兩天還涮了陣小雨,天愈發湛藍,陽光下山體也顯得格外清朗。彎彎的石階順著山勢盤旋,兩旁蘿蔓攀生峭壁,與石縫里的流水相映成趣。“青藤紫葛繞門楣,奇花異草洞內生”。幾尾鳳竹,數簇野菊,把山路綴點得如詩入畫。大山的靈性還淌瀉在石道兩旁的流溪水凼里,處處清洌見底,幾尾浮游的娃娃魚留人踞足,不時地讓山谷回蕩著久遠的童嬉聲。
佇立山坡,迎著陣陣爽人的秋風,仰首遠望,峰映藍天,我心頭一陣潮涌,便大聲呼喚起來,聲音在山谷回蕩,報之陣陣松濤。近了,心中的天柱就在眼前。
接下來的山行是順著蒼翠秀潤中延伸的小徑,時而橫跨潺潺的澗水,時而擠過陡峭的巖坎,一次次地觸及那心跳的回憶,也給人一種登高喜悅的體驗。慢慢地爬上青龍背,貓著身子越過試心橋,抬首望去,前方,久久心儀的天柱峰直如筍尖,一柱擎天,四周千崖萬壑,群峰兀立,拱拜回環。遠方的天格外高,也格外藍,峰頂眾石鼎峙的巒壑叢中,風過瞬間,呈現白霧縷縷,嵐霽萬千,變幻雄奇靈秀。望著眼前的天柱峰,這是何等挺拔,萬仞的絕壁,壘起我心中的天柱,任憑世事幻變,卻沉穩地撐起一方天空。
與我童年好奇不同的是,古往今來的文人名士對這座大山出于一種理性的憧憬。關于這點余秋雨先生在筆下《寂寞天柱山》中已潑墨敘述,不過他講得有點玄乎,所列的人物都似乎對天柱山有一種超然歸宿感和依賴性,甚至提升為“家”的理念,使天柱山成就一種精神意義上的家園。其實秋雨先生過多地停留于文獻檢索,止步在文化的反思里,沒有真正地直擊大山全面目。我承認,他說的天柱山有宗教,有美景,有詩文,但這些不足以成為這座山的經典,不能完全作為名人鐘情于斯的詮釋。
真正讓人折服于天柱山的,還是由于其山體富有極至的內涵。幾千年來文明的承接,在這里掀起的陣陣精神思潮,一次次激蕩了歲月的積淀與厚重的文化底蘊。山麓薛家崗的陶片,繩紋著人類發跡的符號;狼煙四起的諸侯紛爭,皖伯公讓居地百姓能偏安一隅;迎來皇家浩浩蕩蕩的車駕,迎來了信步登山的劉徹,封禪南岳以山作證地炫耀了大漢的“文治武功”。隋詔南岳移湘衡山后,兵燹禍及大山,熱血黃土讓樹木生長得挺立而悲壯。從獰獵到硝煙,繁盛到湮沒,現都如一地化為冷冰冰的摩崖石刻。千年的風騷,千年的平淡,歲月輪回里,大山已黯然潛下。
天柱山也稱為“潛山”。一個“潛”字,讓天柱山沉寂幾多歲月,少了點喧鬧,缺了些繁華。然而只有如此淡泊清幽,才順應了文人廩性,于是有了黃山谷躲進“石牛古洞”,舒州李公麟臨石繪刻,也有了徐霞客的真言,蘇東坡的虔誠,和王荊公的迷戀。
翻開《爾雅•釋言》,“潛,深也。”言簡而雋永,我深深體味古人把天柱山又稱之為“潛山”的妙處。這同一座山,卻有兩個風格迥異的名子,一個是張揚與喧嘩,一個是蘊涵與理性。說實在的,真正看好天柱山不僅僅是其靈性與秀氣,更重要是“山品”如其形,把主峰深藏在群山之中,一種無謂的淡泊至志。“幽巖邃谷,窮之益深,潛之取義也”。我很喜歡潛山這個名字,喻示深藏的美麗。現在看來,小時候與天柱山留下難解的情結是出自一種好奇的話,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才是從心靈深處至真地崇敬。
山上歸來,我細細地品味著白居易的詩句:“天柱一峰擎日月,洞門千仞鎖云雷。玉光白桔相爭秀,金翠佳蓮蕊斗開。時訪左慈高隱處,紫清仙鶴認巢來。”什么時候,我再來細讀心中的山,再次體味天柱的靈秀,天柱的雄渾,天柱的飄逸,和天柱的俊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