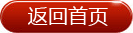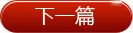我不知道詞典中對(duì)“鄉(xiāng)音”是如何解釋的。這里我望文生義地理解為:同一個(gè)家鄉(xiāng)的人,同一方水土養(yǎng)育下,他們?cè)谡f話口音和某些用語(yǔ)習(xí)慣上共同的特征吧。
中國(guó)人有多少種鄉(xiāng)音?我不知道。記得上大學(xué)時(shí),教現(xiàn)代漢語(yǔ)的先生說全國(guó)說漢語(yǔ)的人可分為8個(gè)方言區(qū)。然而同一方言區(qū)內(nèi)的口音又是千差萬別的。
每一個(gè)城市一般都有自己的方言土語(yǔ),廣闊的農(nóng)村更是走上數(shù)十里往往就能聽到一種或幾種不同的口音。
(二)
鄉(xiāng)音是人們?cè)谕环剿琉B(yǎng)育下的烙印。兩個(gè)流落異地的同鄉(xiāng)人萍水相逢,盡管素不相識(shí),只要一張口說話.他們彼此就會(huì)感到親切無比,心靈之間驟然拉近了距離,如同見了親人。這鄉(xiāng)音會(huì)把他們團(tuán)結(jié)一起,相互關(guān)心,相互救助,共赴難關(guān)。
這時(shí)候.那濃濃的鄉(xiāng)音是多么親切美好。它會(huì)帶給異鄉(xiāng)的游子多少溫馨和甜蜜。
(三)
“少小離家老大回,鄉(xiāng)音未改鬢毛衰。”這是唐代詩(shī)人賀知章的鄉(xiāng)音,千百年來膾炙人口,讀來每每催人淚下。幾許鄉(xiāng)愁,幾許感慨,幾許溫柔都在這未改的鄉(xiāng)音里了。
有這樣一個(gè)電視小品:
一位農(nóng)民企業(yè)家要去歡迎一位歸國(guó)考察投資的老華僑。有關(guān)部門特安排一位禮儀小姐教農(nóng)民企業(yè)家一些社交禮儀。可這位農(nóng)民企業(yè)家卻是膠東口音,侉腔侉調(diào)不說,張口閉口還帶著口頭禪“伙計(jì)”、“伙計(jì)”的。
禮儀小姐費(fèi)了老大勁,才讓他學(xué)會(huì)一句“你好啦一—,趙先生一—”。可是一見面,沒說上三句,他就冒出一聲“伙計(jì)”。正當(dāng)小姐和農(nóng)民企業(yè)家本人都驚愕失語(yǔ)時(shí),老華僑卻一雙手緊緊抓住企業(yè)家的手,激動(dòng)得熱淚盈眶,“伙計(jì)!我整整四十年沒聽到這熟悉親切的鄉(xiāng)音了。”
(四)
常見一些中學(xué)畢業(yè)就出去打工的少男少女們,也不過就出門二三年,再回到家鄉(xiāng)時(shí),早已西裝革履,操著時(shí)髦的粵語(yǔ)京腔了。土生土長(zhǎng)用了十七八年的鄉(xiāng)音早巳和他們出發(fā)前母親千針萬線縫織的衣服鞋襪一樣,因?yàn)樘蝗霑r(shí)而扔進(jìn)了垃圾桶。
誰說“鄉(xiāng)音難改”。
(五)
從未謀面的妻妹,第一次見面時(shí),操著一副外鄉(xiāng)口音,總讓我感到高深莫測(cè),竟莫名其妙地覺得她要比我妻成熟得多。慢慢接觸了她的為人處事,確信妹妹終究是妹妹。
現(xiàn)在她仍舊是那一副口音,再聽起來卻沒有了當(dāng)初那種神秘感。偶爾也掛個(gè)長(zhǎng)途過來,一拿起聽筒,聽到那熟悉卻不甚懂的口音,我就喊妻來。這邊,“什么?什么?”那邊一遍一遍重復(fù)。我又好笑又悲哀,“你們累不累呀?”不過是嫁過去三四年光景,真的一句家鄉(xiāng)話也不會(huì)說了?
(六)
大學(xué)時(shí)代,同班同寢室的學(xué)友也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,慢慢地就聽懂了各自的方言土語(yǔ),也能學(xué)說一點(diǎn)。入鄉(xiāng)隨俗,為交際的方便,我們也都學(xué)會(huì)所在城市的方言土語(yǔ)。
畢業(yè)回鄉(xiāng)工作后,我們一個(gè)個(gè)仍舊是標(biāo)準(zhǔn)的家鄉(xiāng)土話。
領(lǐng)導(dǎo)也曾多次強(qiáng)調(diào)要求用普通話上課。盡管我們進(jìn)行過正規(guī)的普通話訓(xùn)練,會(huì)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,可是一走上課堂總是不自覺地用起了家鄉(xiāng)土話。總覺得用家鄉(xiāng)土話講得親切自然,風(fēng)趣幽默;表達(dá)得淋漓盡致,學(xué)生們喜聞樂見。
也曾因此被領(lǐng)導(dǎo)批評(píng),也曾因此丟掉評(píng)先進(jìn)的資格,然而卻是習(xí)慣成自然,積重難返。
現(xiàn)在,常碰見從前教過的一些學(xué)生,出門打工幾年回來,看他們西裝革履,染色頭發(fā),操著標(biāo)準(zhǔn)的粵語(yǔ)京腔,家鄉(xiāng)土話連一點(diǎn)影子也找不到了。常常不由地感嘆:
真是后生可畏呀!